 【資料圖】
【資料圖】
三年不到,中國人保(601319)的羅熹時代匆匆結束。
年底才滿63歲的羅熹,在“金句”事件后的兩周,被宣布免去中國人保集團黨委書記職務。當天,三大金融機構人事調整,唯羅熹獲得了出圈的關注。
羅熹橫跨銀行保險,歷經農行和工行,以及太平和人保,履歷之豐富,跨度之悠長,屈指可數。60歲北上,躊躇滿志,旋即在人保刮起羅氏旋風,毀譽兼有,爭議從未停歇。
形勢選人,人選形勢。強硬的轉型恰恰撞在疫情墻上,大個險遜色,大銀保崛起,數百萬代理人出走,整個保險業摸石頭過河。穹頂之下,中國人保并未有何不同。
天時地利人和,缺一樣,改革都是易碎品。
欲速不達
在履新后的首場業績發布會上,羅熹火力全開,和盤托出改革方略,喊出人保“重歸C位”的口號。“我們從原來的老大變成現在的老三,誰能服氣啊?不服氣。”
羅熹認為,這里面有能力、體制、技術問題,更重要的是觀念思想問題,“文化改造是不可避免的”。
于是,前任的3411被翻篇了,“湘江突圍”和“三灣改編”應運而生,前者要求堅持大個險戰略,轉向高端人才、高端產品、高端客戶;后者則是硬碰硬的人的調整,包括“5855”,即男性干部和女性干部分別達到58歲和55歲要退居二線;以及“5+2”,即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有5年在保險主業從業經驗,并有2年到基層鍛煉的經歷。
大刀闊斧、雷厲風行,這是業內對于羅熹改革的印象。年輕化和專業化,向來是改革的路徑,但阻力也極大。刀刃向內,一方面需要強勢,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勢。羅氏改革,之所以被側目,就在于時間和勢不在人保這邊,疫情三年,在壽險領域產品不好賣了,增收不增利,基層壓力日甚,改革并沒有帶來惠及絕大多數人的紅利,自然便被視為“折騰”。
事倍功半,逡巡不前,也會影響主政者的心態。“金句”事件有多種解讀角度,但也可以看出“急躁”,為了迅速打開局面,而簡單粗暴地訴諸于形式主義。事情往往是這樣,欲速則不達,不審勢就會生長出反噬自身的力量。
水落石出
2023年,人保在年初的工作會上,提及“保費收入首次突破6000億元,創下了歷史最好盈利業績,充分體現了高質量發展成果”。
但這并不能服眾。
2023年疫情下居家時間變長,財險賠付率普遍下降,全行業的盈利狀況都有改善,作為財險老大,人保受益其中,并不令人意外。大個險則亮點不多,與全行業一樣,同頻共振。當初有多強調“三高”,有多強調價值導向、告別規模至上,現在就有多尷尬,這當然不是人保一家的尷尬。大大小小的壽險公司,都在增長停滯下不得不改弦更張,被高調嫌棄的銀保重歸C位,終身增額壽險等理財性質的保險成為爆款,規模重新成為不約而同的訴求。
人保對此辦法不多。鬧出“金句”事件的人保壽險,在2022年保費負增長。但2023年,疫情成為過去,條條塊塊,都在拼經濟和促消費,都在力爭開門紅,都在高喊開局即決戰,壽險即使內外交困久矣,但已再無借口。人保壽險背不背得出來“金句”是小事,如果保費繼續疲軟,有沒有羅熹,都會繼續刀刃向內了。
事實上,“金句”事件看似偶發,貌似個人使然,其實也是發展困境的折射。就像過去這兩三年,險企自家員工紛紛去社交平臺“舉報”,也是同樣道理,增長放慢,水落石出,問題浮出水面。
其惟春秋
羅熹赴任之初,中國人保正焦頭爛額,信用證保險屢屢踩雷,又陷入武漢“黃金案”的輿論泥沼,羅熹手起刀落,廓清外圍,并快速錨定新的航向。
兩年前,羅熹在業績說明會上表示,舊的保險模式只會形成規模的適當增長,但它不會呈現出一種跨越式的增長和形態、模式上的變化。
兩年過去了,這仍是人保甚至中國保險業的現狀。所謂有增長無發展、大規模同質化發展,怎么破?大健康、數字化、服務升級,說起來頭頭是道,道理都懂,但轉化為市場行動力,卻又很難。這或許就是創新的荊棘和玫瑰所在吧。
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,金融老兵也不例外。“金句”事件固然沸騰,個人風格頗有微詞,但于圈內人而言,保險業高質量發展,迫在眉睫。
知我罪我,其惟春秋。
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:A智慧保。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,不代表和訊網立場。投資者據此操作,風險請自擔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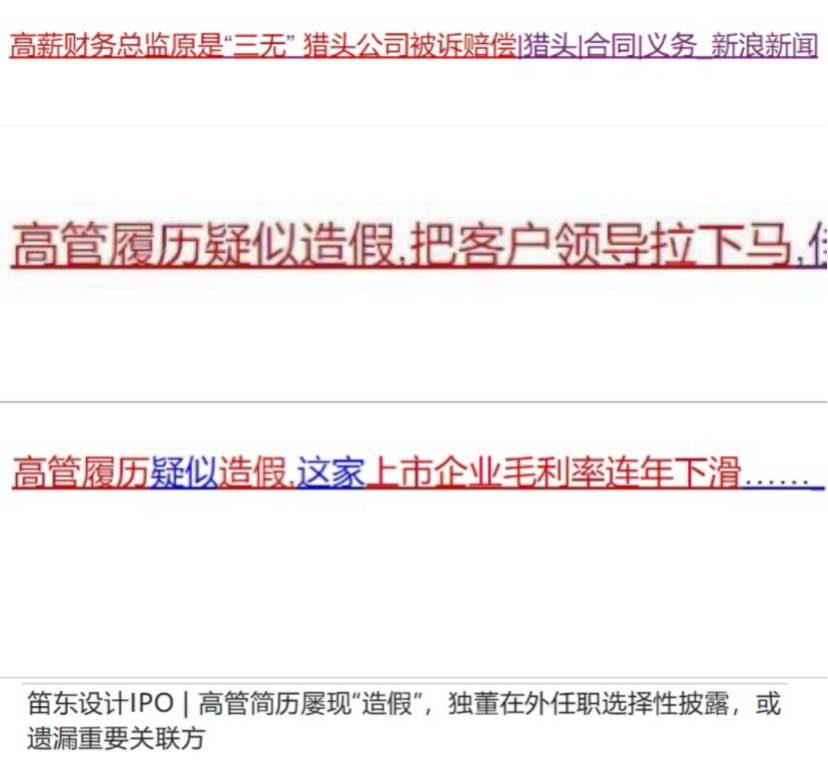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
營業執照公示信息